- 厅局主页
2023年仲夏,当上海交大的梧桐叶簌簌落在学位服上时,秉承着“饮水思源”的校训,我攥着写有“服务国家战略”的毕业纪念册,踏上了Z172次列车,回到了我的家乡黑龙江。车厢外的风景像一卷徐徐展开的《千里江山图》,而我的行囊里,装着朱熹“问渠那得清如许”的思索,更装着王阳明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”的赤诚。
作为一名定向选调生,经过了一年时间在机关的试用期,我被安排到哈尔滨市香坊区朝阳镇东升村工作锻炼。初至东升村时,黑土地翻涌的泥土香扑面而来,这份熟悉的亲切感背后,是更深沉的叩问——我能为这片土地留下什么?三百个日夜轮回,我在晨露未晞时走访老乡,在暮色四合时记录民情,与老支书畅谈乡村振兴的棋局,跟菜农学习大棚作物的“呼吸节奏”。当稻浪再次涌向天际线,我终于读懂了土地的语言:所谓反哺,不过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,用脚步丈量民情,以真心交换真心。基层这本无字书,教会我最朴实的真理:扎根越深,收获越丰。
将脚印刻到村里的每一个角落,我从“大学生”变成了“小林的”。初到村里时,村民们总用“大学生”这个标签打量我,这三个字里藏着好奇与距离。直到我的笔记本记满了田间地头的数据,直到我能在暴雨来临时准确报出每处危房的位置,直到调解完纠纷后村民端来那碗热乎的玉米糊——他们开始叫我“小林的”,这个称呼里裹着泥土的温度。我用三个月走遍了村里的巷道,在走访中发现了王大爷家危墙下的排水隐患,在统计留守儿童数据时摸清了李婶家因病致贫的症结。当我把这些信息织进村情调研报告时,那些原本躺在表格里的数字突然有了呼吸。跟着老支书处理土地纠纷时,我学会了“打圆场”的智慧,明白了为什么村东头的老井必须保留,村西头的歪脖树隐藏着怎么样的故事,这些看不见的“路标”,才是基层工作的真正导航。现在每次路过村口小卖部,张婶总会喊:“小林的,来尝尝新摘的西瓜!”这声呼唤里,早已没有最初的生分。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,最终都化成了村民信任的刻度。基层这本大书,从来不是用来翻阅的,而是要用脚步一页页丈量。当“小林的”这个称呼在村里传开时,我才明白:真正的成长,始于离开书斋走进田埂的那一刻。
认真调研美丽乡村建设在产粮村的实施路径,我从“选调生”变成了“研究员”。按照定向选调生的培养要求,我需要在驻村期间完成一项国情调研课题。当看到村委会墙上“粮食安全示范村”的铜牌与田间杂乱堆放的秸秆形成刺眼对比时,我决定以"产粮型村庄美丽乡村实施路径"为研究方向——这不是个学术选择,而是站在晒谷场上,看着村民们用开裂的手掌摩挲着稻穗时,突然明白的研究使命。最初的调研遭遇了“水土不服”,按照指南要求“一户一景”,但村民老李直接撕了问卷:“我家晒谷场都没地儿,种什么花?”这记当头棒喝让我扔掉预设框架,改用“粮农语言”重构研究体系,随着调研数据的增加,一个关键认知逐渐浮现出来:产粮村的“美丽”必须首先解决“生存性矛盾”。在收集了583份有效样本后,研究发生了质变。我发现问题的核心不是缺政策,而是缺乏“粮农思维”的转化通道。比如村民对“垃圾分类”的抗拒,本质是担心影响有机肥制作;“庭院经济”推不开,实则是晾晒空间不足。于是我计划将学术概念翻译成乡土方案:用稻壳压制环保建材替代传统砖墙,设计可移动式晾晒架兼顾庭院美化与粮食干燥。现在的我完成了双重蜕变——不仅是完成了从选调生到研究员的知识转型,更真正读懂了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:所有研究都必须先在泥土里完成从“种子”到“粮食”的转化。
当驻村工作手册翻到最后一页,那些浸着露水的晨访记录、沾着稻香的调研笔记,突然都变成了沉甸甸的成长印记。这一年,我像一株被移栽到黑土地上的树苗,在乡亲们“你比咱家小子还懂种地”的玩笑声里,完成了从“机关干部”到“村里人”的身份蜕变。
于驻村工作的尾声回望,这片黑土地教会我的,远比任何理论课程都深刻。走进人民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,从最初的纸上谈兵,到如今能精准测算一亩地的秸秆还田效益,这一年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,让我真正读懂了“光耀黑土”的新时代含义,就是实干,把论文写在大地上,把青春献给乡村振兴。来到新的岗位,但驻村时老支书那句“黑土养人,更要人养黑土”始终萦绕耳畔。非常荣幸可以用我在外面学到的知识和经验,来反哺生我养我的黑土地,未来我将继续践行“光耀黑土”的使命,让青春在龙江振兴的沃土中绽放光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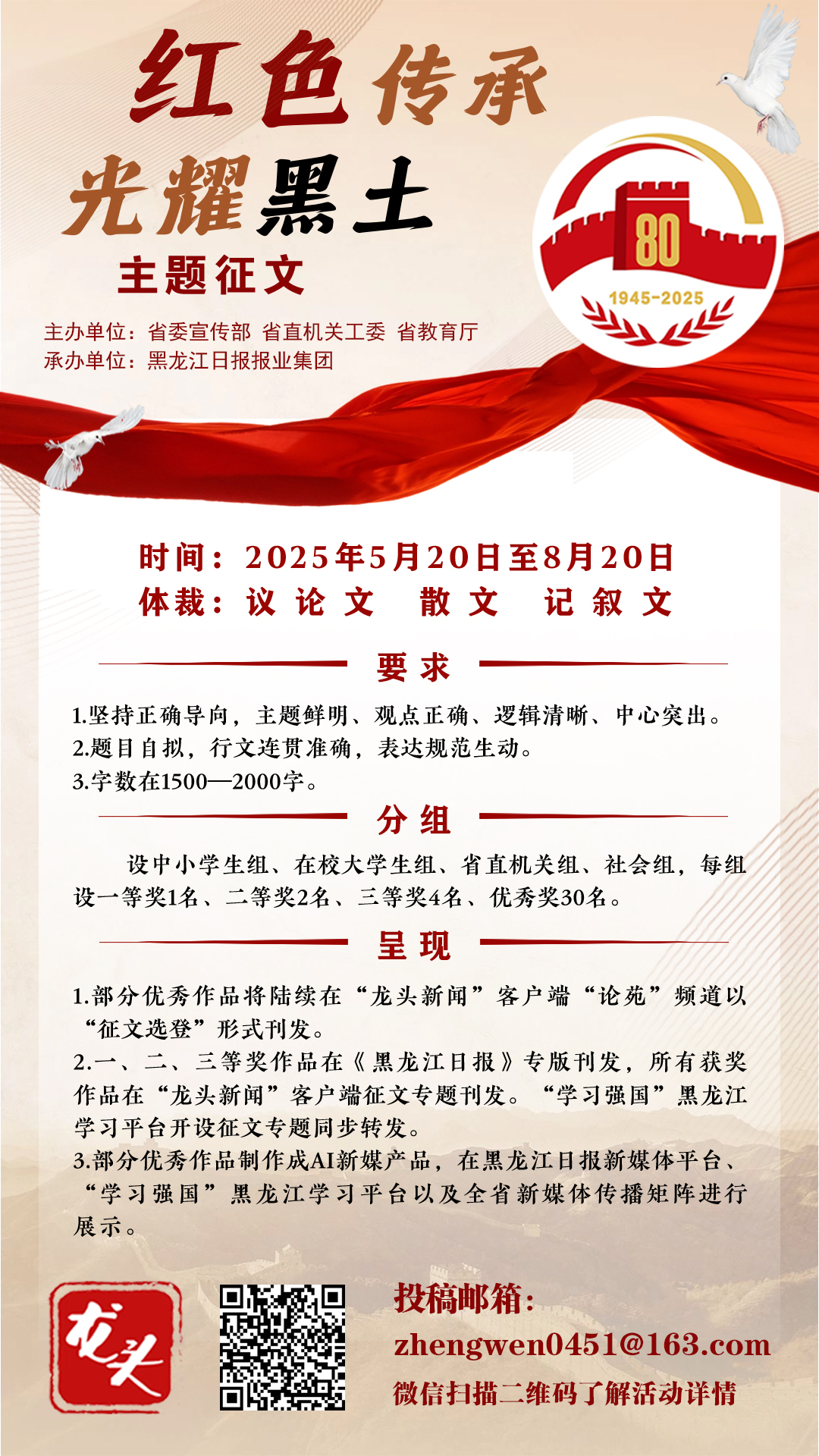
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
来稿选登与获奖无关,也不作为晋级依据
作者: 省政府办公厅 林宇肖
【版权声明】凡来源中注明“龙江机关党建”的文章,均为本网独家稿件,版权归龙江机关党建所有。
主办单位:中共黑龙江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技术支持:黑龙江广播电视台(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)
联系电话:0451-87589289
